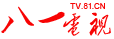最后的心愿
一轮朝阳,冉冉升起。金色的光洒在玉渊潭公园的湖面。湖边,早春的樱花争相绽放,晨练的人们时不时拿起手机,拍下明媚晨光中的花影。
距离这不远的地方,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的一间病房里,一位94岁的老人安详地合上了双眼。从全国各地赶来的5个儿女,为他穿好心爱的军装,泣不成声。
这一天,是2018年3月28日。
周智夫——一个在旧社会长大的穷苦孩子,一个在抗日战争中浴血奋战的战士,一个有着75年党龄的老党员,一个从旧时代走来、见证新时代的老兵,在这样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,平静地离开了。
周智夫走了,走得很幸福——
“我比那些牺牲的战友幸运,我活下来了。活了这么久,活得很幸福。”这是周智夫生前常挂在嘴边的话。
“我没有遗憾了。”这是周智夫躺在病床上了却最后的心愿时,对家人说的话。
这位老人最后的心愿究竟是什么?
是想见远方未能回来的儿孙,还是想再看看当年征战沙场的照片?
都不是。
答案就在那张鲜红的大额党费收据里——2018年初,病重的周智夫委托家人向党组织交上了12万元大额党费,“这是连这辈子剩余的,带下辈子的党费”。二女儿周卫平说,当父亲用颤抖的双手,轻轻捏住党费收据时,还戴着氧气面罩的他,眼神中满是激动。
周智夫,这位94岁的老兵,在生命的最后时刻,用最朴素的行为,表达一名党员最朴素的想法——此生报国无憾矣。
一、老兵最自豪、最传奇的军旅人生,浓缩在那一枚枚军功章里
周智夫的儿女们都知道,父亲最宝贝的东西都藏在一个小木盒里,而这个深褐色的小木盒又被藏在家中那个大衣柜的夹层抽屉。如果岁月可以被收纳起来,周智夫最自豪、最传奇的那段军旅人生,便都存放于此。
打开小木盒,来自战场的硝烟与轰鸣从中弥漫开来,那淹没于历史深处的枪林弹雨,仿佛一下子又扑面而来。
盒子里装的,是周智夫的军功章。
解放奖章是一枚小小的金色胸章,红色的五角星在天安门城楼上放着光芒。虽然已经过去了70多年,这枚解放奖章看起来却仿佛还是崭新的,缀在正中央的鲜红五角星色彩依旧。这枚颁发于1955年的奖章,成为周智夫参加解放战争的坚实注脚。
比奖章更为深刻的,是留在他右胸下部一个长达10厘米的凹陷。
1946年,国民党军队兵临安徽豪城外。时任新四军淮北七分区独立四团二营四连支部书记的周智夫,和战友们守着城里的粮食。战役打响之前,周智夫跟战友们说:“若是这粮食被抢去了,那意味着豪城也将失守。豪城失守了,国民党就会像洪水一样北上。”
子弹直面而来的时候,周智夫正向不远处的一名敌人举枪射击。
“砰!”子弹以高速在周智夫的左肩上旋开一个口子,来不及反应,子弹又顺着轨迹贯通了周智夫的右肺,接着冲出他的身体,径直插入他身后通信员的小腿。鲜血很快将他们的衣服染透。
再睁开眼时,周智夫意识到自己躺在后方医院里。他缓了一下神,想要坐起来,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动弹的力气。不仅如此,撕心裂肺的剧痛逐渐蔓延全身。
周智夫的“撕心裂肺”是真的撕心裂肺——这个贯通伤让他失去了右侧第六根肋骨,以及进三分之二的右肺叶。不过幸运的是,“战友们冒着枪林弹雨把他抬下战场”,让他活了下来。可是,在生死一线的战争中,这样的事情即便称得上幸运,也很难让人感到轻松。
和周智夫一起负伤的通信员,截肢了。没过多久,这名通信员伤口感染,病情不断恶化,几天后牺牲在医院里。
敌人的炮火震碎了医院的门窗。医生、护士和周智夫的战友们,抬起担架转移阵地。刚刚做过几次大手术的周智夫无法行走,就这样被战友们抬着,一路北上。许多次,他望着天空中弥漫的硝烟,眼角不自觉地淌出泪水。
经历了大大小小数次手术,被战友们抬着、搀着,一路从苏北辗转至东北。只有20几岁的周智夫,明白了什么叫“九死一生”,心中也永远地刻下一个信念:“我的命,是组织给的”。
外孙周洵在5岁的时候,第一次碰触姥爷身上这道“可怕的伤疤”。懵懂之中,姥爷第一次给他讲了“打仗的故事”,“虽然不太懂,可依然觉得很神圣”。再次触碰,是2011年周洵第一次带新婚妻子去探望他。
看着一手带大的外孙成家立业,一向少与小辈交流的周智夫打开了话匣子,从苦难的童年讲到安享的晚年。讲完后,周智夫郑重地将两个年轻人的手交叠在一起,说:“你们要好好的。”
周洵第一次觉得,这个像极了电视剧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里石光荣的老头,这个小时候对自己严苛到连吃饭时间都要规定的老头,这个天天捧着报纸、看电视只看新闻的老头,老了。刚刚过去的四十分钟,就像是自己的一场成人礼。那双干枯的大手,仿佛给自己传递了一种力量,传递一颗家族的火种。
周洵曾想向姥爷讨一枚军功章做纪念,妈妈告诉他,趁早打消这样的念头。“那几枚军功章,姥爷看得比命还重”。
二、时光让他身上的老军装褪了色,却没有让他的心褪色
周智夫的家中,有一个黄色木纹的衣柜。这个上世纪80年代的时髦物件,现在成了“老古董”。可摆在周智夫简朴的家中,也并不显得突兀。
柜子里,挂着周智夫最爱穿的军装,一共3身,他却只换穿其中两套。他觉得,“有的换洗,两套足够”。两套老式军装的袖口和领口都有磨损,但却干干净净,平平整整。而另一套崭新崭新地挂在柜子里,直到他离开,也没上过身。
阳台上,放着两把藤椅。如今,空了一把。
料理完周智夫的后事,老伴娄淑珍依然会像从前一样,每天坐在藤椅上晒晒太阳,看看楼下车水马龙。有时,一坐就是半天。
结婚的时候,周智夫17岁,娄淑珍19岁。没过两年,周智夫就秘密入了党,参加了革命。知道丈夫受了重伤,娄淑珍带着年纪尚小的大儿子去看他。没待多久,就赶紧回家去了,“家中还有公婆,孩子还太小,哪里都离不开”。
就这样等呀,盼呀,终于,再见到丈夫的时刻,这个坚强的、“从不掉泪”的女人,趴在丈夫肩头,哭成了泪人儿。多年的心酸与委屈,随着泪水倾泻而出,一点一滴渗进了丈夫的军装里。
最大的苦,并非来自生活,而是你不在身边。有你陪伴的日子,再多坎坷,也是幸福。往后的日子里,每一次都是周智夫到新单位一安顿好,娄淑珍就领着孩子、拖着行李追随而来,从南京到重庆,从重庆到云南,从云南再到北京。
即使漂泊,有你,便是家。
生活一天天变好,周智夫却发现身边有些人开始有了变化。他试图去劝解,却碰了一鼻子灰。
回到家,周智夫一把拉起正在洗衣服的娄淑珍,紧紧握住她湿答答的手说:“我绝对不会变心,我们要好好的,要白头到老!”
娄淑珍被丈夫突如其来的表白“吓了一跳”,楞了会儿神,两朵红晕在脸颊泛了开来。
坐在藤椅上的娄淑珍一脸幸福地回忆着过往,时不时抬起手缕一缕星光色的头发,然后笑呵呵地对我说:“你看,这不是就白头到老了吗?”
儿女们对父母的恩爱习以为常。“我妈做饭,我爸洗碗,这么多年一直如此。”从江苏赶回来的小儿子周卫民对我说。
“周老做饭吗?”我问。
娄淑珍一听,乐了:“我不在家的时候,他自己会下面条。有时候,他做到一半,我回来了,他就一抹手说,还是你来做,我来洗碗。”
看着两只眼睛笑成两牙弯月的娄奶奶,我的眼睛有些湿润。生活磨去了他们的棱角,磨掉了他们的激情,却把他们的感情打磨得温润而纯粹。
有时,儿女们会看到娄淑珍一个人坐在周智夫的病床上,用手轻轻抚摸那一身她不知洗过多少回的军装。
摸着摸着,眼泪就掉下来,一如当年,渗进他那褪了色的旧军装。
三、在党员的角色中,他是“无情”的;在父亲的角色中,他是温情的
二女儿周卫平最遗憾的事,就是搬家时弄丢了那个木箱子。
那是一个极普通、甚至做工有些粗糙的木箱子,却也是父亲亲手为她打的木箱子——箱子的木板,是他们从重庆搬家时,用来保护家具的木板;箱子的合页,是家中不知做什么东西剩下的两块碎皮料。
17岁那年,周卫平中学毕业。看着周围的小伙伴一个个“消失”,她和妹妹周卫华四处去打听。最后,她们知道,小伙伴们都当兵去了。
姐妹俩相差一岁,想法想通,挑了周智夫在家休息的一天,同时跟父亲开了口:“爸,送我们去当兵吧!”
周智夫一听,停下手里的活,上下打量着眼前的小姐俩。
周卫平和周卫华从小没离开过父母。大儿子周华十几岁时,就自己去参了军,转业之后留在了江西;大女儿周雪文,在他们举家离开重庆前参加了工作,周智夫任凭周雪文怎么在信中哭诉孤独和难过,也不肯让她辞工去云南找他们;小儿子周卫民在毕业之后,听了父亲的话,“在哪里都能闯出一片天”,在云南退伍之后,只身回到江苏老家去创业。如今,只剩这对姐妹在他们身边了。
周卫平被盯得心里有点发毛,她又开口道:“你是不是舍不得我们离开?”
“你哥哥姐姐我都没让留在身边,我会舍不得你?”周智夫回答。
“那是为什么啊?我们当兵,这不就是您开口两句话的事儿吗?”周卫平不依不饶。
周智夫刚刚面无表情的脸上,立马露出了愤怒的神情:“别说两句话,就是一句话,我也不给你开这个后门!”说完,一转身出了屋。
周卫平心里郁闷极了,心想自己怎么不是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一连几天,她都有些赌气。直到有一天晚上,她一回家便说:“我要去插队!”
周智夫沉默了几秒,说:“去吧,插队也挺好,一样锻炼人。”
娄淑珍知道事情原委,却也不开口劝。多年来,她习惯了周智夫的行事作风,也习惯了让孩子们去自力更生。
星期天,周卫平吃过午饭便出去找同学散心。下午回家一进院子,就看见父亲手拉大锯在锯木板。她从来没见过父亲做木匠活,这会儿是要干嘛?
院子里叮叮当当一阵响。
“小卫平,你来看看,这个箱子怎么样?”周智夫一边抹汗,一边笑嘻嘻地问周卫平。
“好呀,真好!爸爸,你还有这手艺呢!”周卫平用手摸摸皮带合页,笑着回答。
“那送给你插队用,你觉得怎么样?”
“真的吗?这是送给我的箱子吗?”周卫平喜出望外,之前心里的气一下子消了。
“那时候,能有个属于自己的箱子,那绝对是奢侈品!”现在的周卫平早已两鬓斑白,可说起父亲给她打的木箱子,眼里还会闪着小女孩儿般的开心。
周卫平将箱子内壁贴上一层纸,把衣物小心翼翼地放进去。箱盖一锁,小姑娘趴在箱子上傻乐。于是,这只两尺见方的小木箱,成了周卫平最宝贝的东西。一把小锁头,锁着周卫平所有“值钱的物件”,锁着少女的心事,也锁着周智夫作为一位父亲的温情。
父亲走了,木箱子丢了。周卫平觉得这是她最大的遗憾。
曾经,她怪父亲不肯为了自己放下原则,直到父亲生病住院,她有时还会嗔怪父亲的“抠门”。如今,凝视着家中父亲的遗照,他那正气凛然脸上布满沟壑,如同时间挖下的战壕,见证了变迁,见证了岁月。
周卫平懂得了父亲。
讲完木箱子的故事,周卫平透过窗户望向远方。一转脸,她的眼眶内已经满是泪水,她说:“爸爸住院时,有一天对我说,小卫平啊,如果我走了,我会很想念你们的。”
四、走过旧时代,来到新时代,这名老兵从没忘记肩上的使命
直到现在,周智夫的卧室仍保持着他住院前的样貌——
窗台上摞着四本他正在读的书,最上面一本是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》;一台小电视,放在离床两米远的地方,一打开,还是他之前看的新闻频道;床头柜和大黄立柜的年纪相当,深褐色的柜门已经没法关严。因为周智夫常用的新华字典、放大镜等全放在里面。柜面上,还摆放着周智夫去年收到的一件小礼物,这件小礼物“不值钱”,周智夫却爱不释手。
那是一个金紫荆花造型的音乐盒,上面的塑料包装袋仍保存完好。可仔细一看才发现,包装被打开过许多次,不干胶早就失效了。
小女儿周卫华看着音乐盒,眼前总会浮现出父亲开心的笑容。
2017年6月,周卫华跟着旅行团来到香港。旅游大巴车上,导游拿出音乐盒开始兜售:“现在大家手中的音乐盒,是香港的地标建筑——金紫荆雕塑的微缩版。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,中央政府把雕塑送给香港,寓意香港将永远繁荣稳定。”
周卫华仔细端详着手里的这个小东西,心里盘算着一件事。
这时,导游接着说:“打开它,音乐盒就会奏唱国歌。”说着,导游打开隐藏在底座下的开关,铿锵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飘荡在车内。
周卫华听到第一个音符的瞬间,将手揣进口袋,掏出20块钱,买下了它。
“我知道,我爸爸一定会喜欢的。”周卫华笃定地告诉我。
后来,周智夫的反应印证了女儿周卫华的预言。捧着音乐盒,周智夫看了又看。他从没去过香港,可是他在电视里看过许许多多次这朵美丽绽放的金紫荆。周卫华轻轻拨动底座开关,打开音乐盒。
“当时,我爸爸的眼睛都亮了!”
周智夫把音乐盒里飘出的国歌声听了一遍又一遍,直到周卫华告诉他,没电就听不了了,他才关上开关。从此,这个音乐盒也成为周智夫最常用的东西,陪伴他度过了生命最后的一段岁月。
现在,再打开音乐盒,飘出的国歌声因为电量不足变得沙哑。但一如周智夫的双手,枯瘦,却有力;一如他的眼神,日渐浑浊,却依旧坚定。
暮年时的周智夫,时常会打开装满军功章的小盒子。看着自己的军功章,跟老伴儿说:“要是那小通信员还活着,现在也是儿孙满堂了。”
娄淑珍坐在他身边,静静听他说着,她知道,没能找到牺牲通信员唯一的哥哥,是丈夫心里的一个结。所以,这些年,他这么努力,这么执着,这么坚持,这么“固执”。那为今日之和平流过的鲜血里,有他自己的一份,有他战友的一份。
2015年九三阅兵前一天,干休所将又一枚闪亮的勋章送到周智夫的手上,上面写着: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。
周智夫激动地话都说不出来,拿着纪念章的双手不停颤抖。家人想要接过勋章瞧瞧,被周智夫一手挡开。那是一枚没有他的允许谁都不能碰的神圣勋章。
阅兵当天,周智夫早早起床。吃过早饭,站在镜子前认真整理身上的军装和那顶呢子军帽。然后,小心翼翼地从盒子里取出纪念勋章,郑重其事地挂在胸前,连挂绳都整理得平平整整。他腰杆挺得笔直,端坐在电视机前,双手并拢放在膝盖上。那坐姿,一如当年坐在小马扎上的那个小新兵一样。
二女儿周卫平说,那天在老兵方阵通过天安门时,父亲缓缓抬起右手,颤抖着敬了一个长长的军礼。
后记
采访第5天,我们单独到周智夫家拍摄。
一进门,我还是像上次来一样,面对周老的遗像鞠了三个躬。就在我最后起身的那一瞬间,我突然明白了周老最后的心愿。
12万,对于周老的家庭来说,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可他仍愿意在弥留之际将它作为特别的党费交给组织。
其实,周老是将这笔党费交给了自己毕生的信仰与信念。
这,是一份经过血与火淬炼的信仰;
这,是一份经过九死一生烙下的信念。
穿越时代,这份信念历久弥新,愈加坚定。
2016年,周智夫的重外孙远赴海外求学。在北京中转时,一家人来探望他。时年92岁的他,拉着10岁重外孙的手说:“记住,你的根在中国,学成后要回来报效国家。”
看到重外孙认真地点头,周智夫欣慰地笑了。那一刻,他想起自己这么大的时候——在江南老家村里的那座简陋学堂里,窗外下着细雨,他和同学们齐声朗读着先生教他们的那篇文章: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