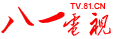爷爷在党七十年
■李雨峰

徐金鑫绘
新中国成立后,老家的村里成立村委会,17岁的爷爷成为村干部,并于两年后入了党。说起入党,爷爷都会深情地回忆:“我要像‘表哥’那样,死也光荣!”
爷爷所说的“表哥”,在爷爷小时候,经常深夜带人来家里“嚓嚓话”(沧州方言,指“小声说话”)。“表哥”平时睡觉没个准地方,又受了湿气,长了一身疥疮,后来便住在爷爷家养身体。老家的沙土炒热以后,是天然的消毒杀菌干燥剂,当年的新生儿都睡这种“土裤”,相当于今天的“尿不湿”。太奶奶便每晚炒沙土,让“表哥”睡在上面拔湿气。
天气好的时候,太奶奶会喊“表哥”出来晒太阳。每到这时,爷爷就抢着给他搓烟叶、卷烟筒,让他讲一些打鬼子、除汉奸的故事。“表哥”讲过的武工队端鬼子据点、活捉日本兵的故事,爷爷印象最深,对他充满敬佩。
后来,敌人来村里大搜查,为了不连累爷爷一家,“表哥”病还没好利索就不辞而别。不幸的是,没过多久,“表哥”被捕,受尽折磨。
太奶奶对此十分自责,很长时间吃不下饭、睡不好觉。爷爷这时候才知道,“表哥”是共产党员。
爷爷当村干部,用他自己的话说,是给大伙儿跑腿的。村民家里不管有什么事,只要找到他,他一定竭尽全力,并且始终坚持一条:绝不占个人或者公家的便宜。哪怕是粮食极度紧缺的条件下,爷爷也从来不往家里多拿一点儿粮食。
对于侵占集体财物、损害群众利益的人和事,他也一定斗争到底。村里有一个村民,依仗着自己跟村支书是亲戚关系,经常明里暗里侵占集体东西。有一次,村里的保卫人员发现他偷了生产队的玉米,按照规定没收了作案工具和所得,但他不依不饶,带着老婆在村子里骂大街,还跑到支书家里“恶人先告状”。时任治保主任的爷爷知道这件事后,十分生气,带着保卫人员硬是把他们两口子关在村委会进行了三天的学习教育。其间,不论谁求情,他都不让步。这件事让全村人都打心眼里佩服。爷爷说:“党员干部不能有私心,该得罪的人就得得罪,当老好人,群众不会赞成你。”
闲谈中,耿直的爷爷也讲起了一件他一直认为“不光彩”的事情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,村里接到了上交三万斤粮食的任务。当时村里的粮食十分紧张,一旦全部拿出,村民们极有可能挨不过冬天。村干部们急得天天晚上集合在村外壕沟里秘密地开会,一个个抽闷烟。爷爷当时是副村长。他经过反复考虑,觉得作为党员不能不讲实事求是,便带着几个村干部一起把库房里的粮食留出一部分,秘密存放好。
如今说起这事,爷爷还是有些不安。因为在他看来,自己做了一件对党组织“不老实”的事。我问他:“如果你真为这事坐大牢,后悔吗?”他叹了口气说:“谁叫咱是党员呢!关键时候,党员就得为群众担事,真饿死人,那才是大事。”
爷爷受“表哥”影响的远不止是对党的感情、做党员的担当,还有他对知识的渴望、对参军的执着。
在家里生活压力最大的时候,爷爷始终坚信有文化才有出息,咬着牙供他的妹妹和五个孩子上学,没有让任何人因为家里困难辍学,并把我的大伯、父亲、小叔先后送进了军营。用爷爷的话说,当兵是报国最好的办法。
2016年,我考上军校。爷爷知道后,高兴得像个孩子。他从枕头下的红布包里拿出来一枚泛着红光的铜弹壳交给我,说:“这是当年我‘表哥’留给我作纪念的,我有两个,一个在你大伯当兵那年送给他了,你是孙辈里第一个当兵的,这个就送给你!记住,你手里的枪是保卫全中国老百姓的。”
进入军校后,不论是在“好汉坡”上挥汗如雨,还是在搏击场上奋力厮杀,我都咬紧牙关,奋勇争先。我不仅很快适应了军校的训练和生活,还取得了一些成绩。大三那年,我入了党。当我告诉爷爷这个消息时,他伸手比着一个“八”字,大声跟我说:“你是咱家第8个党员啦!”
这些年,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家家户户都住进了宽敞明亮的大房子,爷爷还坚持住在他的老房子里。年轻人种地实现了机械化,爷爷成了村里最后一个赶着驴子、拉车种地的人。他养的驴子也成了村里孩子们争相观看的稀罕物。对此,爷爷打趣地说:“我现在成了‘落后分子’了。”
2019年的一个大手术后,爷爷不能再干重体力活儿,但他仍然坚持拄着拐棍喂鸡喂羊,坐着小马扎种菜浇园,开着轮椅车赶集卖菜。村里人劝他歇歇,爷爷说:“人活着就得干活,图清闲享受,人就废了。”大家听了十分赞同。
现在,我家有4人参军、9名党员,爷爷对此十分骄傲。他经常嘱咐我们:“党员不能图个虚名,不实打实地带头干,群众不赞成,那叫什么党员?军人在关键时刻豁不出命,那就不合格啊!”
前段日子,听说党中央要颁发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,爷爷兴奋得连连说:“我入党整整70年!”满脸的皱纹堆成了一朵花。